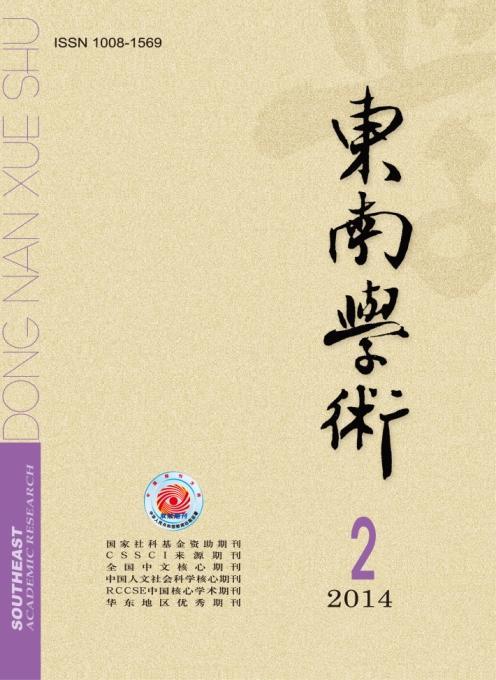
在批判与建构之间:跨文化形象学的两张面孔
林曦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摘要:在批判西方中国形象中隐含着“东方主义”情结的同时,周宁尝试着提出了两种建构性的解决方案,笔者称之为“与权力联姻”及“超脱于权力”的进路。之所以提出这样两个貌似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解决方案,其原因是在于周宁本身在建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本文从对“同情式理解”的视角出发,对跨文化形象学这两张相异面孔进行了一个评述。
关键词:民族主义、权力、超越性、全球主义
Between Critique and Construction: The Janus Faces of Transcultural Studies of Representation
Lin X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In critiquing Orientalism as implicated in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Zhou Ning attempts to suggest two constructive proposals, namely the approach of “marriage with power” and that of “detachment from power”. The reason that Zhou suggests these two solutions that are seemingly in conflict and mutually antithetical is his ambiguity in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offers an analytical account of these two faces of the transcultural studies of im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Keywords: nationalism, power, transcendence, cosmopolitanism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不论是对西方建构“中国形象”的批判,还是分析这一形象在全球化时代的传播和复制,都离不开周宁提出的核心问题——“东方他者”(the Oriental Other)问题。周宁沿着萨义德和福柯的理论进路前进,认为长期以来,小到中国、大到整个非西方世界,都是被当做“东方”,作为“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他者,在差异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西方的所谓‘本质’与价值。西方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东方的表述和表达,创造了所谓西方的东方形象,而东方也正是在这种既定的、体现着西方观念与价值的话语或形象体 系中呈现自身的。这样,东方不过是西方文化创造的‘东方’,不管 是作为地理区域还是文化观念,都是西方历史文化的‘构建物’,而且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为西方而存在、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存在的”[1]。这一“东方他者”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其原因在于通过这种本质主义的东方概念,东方“变成殖民话语的知识与权力的对象,变成西方文明永恒不变的‘他者’,从而确立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秩序中的‘欧洲对东方的霸权’”[2]。因此,“东方他者”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西方借助这一创造出来的概念,来推行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践,为其披上“合法化”的外衣(the vestiture of legitimation)。
那么,面对这一“东方他者”问题,周宁在批判的同时,是否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周宁虽然着墨不多,但是的确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关的思考,这一点在他的文本当中有所体现。但同时,他也遇到了建构之中的一个难题,我把它归纳为“权力关系难题”——具体而言,在挑战这种“东方他者”秩序之时,我们是要选择同权力进行联姻,还是选择一个超脱于权力的立场?如果我们的选择是前者,那么,以何种方式联姻?吊诡的是,虽然这两个解决方案是相左的,但是,周宁在他的文本中同时提出了这两个解决方案,笔者称之为“跨文化形象学的两张面孔(the Janus faces)”。
一、跨文化形象学的第一张面孔——“与权力联姻”
首先,周宁暗示说,我们应当与权力联姻,来破解这一“东方他者”的困局。“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研究对象是‘思想’或‘想象’,方法是学理性的、观念史的,而研究的问题却是当下国际文化与地缘政治战略的,如何使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国家战略研究结合起来?”[3]我们应当注意到,“地缘政治战略”这个词汇在周宁的文本中重复出现过,但是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在其文本的前面,周宁论述道,“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拥有的话语霸权值得关注, 这不仅是一个后殖民主义的文化问题,也是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问题”[4]。显然,此处周宁使用“地缘政治战略”是在相对中性、学术的意义上,因为文化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的重合,恐怕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问题是再突出不过了。因此,周宁将两者并列,其实还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进行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相比之下,他在后面使用“地缘政治战略”,则是目标直指“使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国家战略研究结合起来”,这已经是着眼于把研究和国家权力结合起来,这就已经不是在一种中性的意义上来使用“地缘政治战略”这一词汇,相反,而是在一种政治的意义上来使用。所谓“政治意义”,按照福柯的看法,指的是“知识分子运用知识、能力以及自己与真理的关系来达到政治目的”[5]。
周宁使用该词汇的“政治意义”之处在于,如果我们要想达到“使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国家战略研究结合起来”,就必须要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国家的战略,通过国家权力来实践该“战略”,从而达到解决的目的。因此,从逻辑链条上看,要想达到“与权力联姻”的目的,首先一步就是“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战略”,然后第二步才是“运用国家权力来实施该战略”。周宁只是在这里提出了我们踏出第一步的建议,而并未进一步说明第二步应该怎么做,即我们要如何“运用国家权力来实施”的问题。但是,他在文中他处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我们不妨根据这些线索来大胆推测一下周宁可能认同的“第二步”做法。
周宁在之前的论述中,将美国和中国做了一个对比,他追问如下问题:“当今世界真正的‘威胁’是美国,美国在全世界130个国家驻军或建有军事基地,但为什么没有‘美国威胁论’?中国的全球发展谨小慎微,却惹起美国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在全球范围内甚嚣尘上?如何自身强大又不表现成对他人的威胁呢?”周宁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国家能够为自己提供一套“合法化”的说法,赋予国家力量以合法性[6],这才是所谓“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意义之所在。在美国的这个案例中,为其实力提供“合法性”的是美国所宣扬的那一套“普世价值”,这样的一套“普世价值”当然是和启蒙时代所构建起来的“现代性世界秩序语境”有关,即: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是实现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价值,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在这一个前进谱系当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由于中国的发展路径不在这个“启蒙合法性”的谱系之内,因此没有获得相应的“合法化支持”,从而中国国家实力的成长被视为对这一“现代性世界秩序”的“威胁”。因此,不符合这些“启蒙道理”的国家实力,就是一种“不正义”的实力,就应当被排斥、被视为“威胁”[7]。
仅从这一段的论述,我们很难看出周宁对这种“现代性世界秩序”的态度,但是从其一贯的批判立场来看,我们可以假设,周宁应当是同样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如此一来,这种“普世价值”必然是以西方国家实力做后盾而得以推行的一整套价值观,周宁此间就必然隐含了对这种“价值与权力联姻”的批判,这就从根本意义上否定了西方的这一套价值观会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具有“普世性”。那么,之所以要挑战这种“普世性”,目的是为接下来“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反戈一击”埋下伏笔。既然我们不用承认西方价值的普世性,既然我们看到这套价值在推广过程中与权力的联姻,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弱势国家”而言,我们可以同样提出一套自己的说法,为自己的实力提供“合法性”,并且用权力来推行这一套“反话语”或者“反价值”。因此,结合这一段文字,我们大可以推测,周宁会认同的“第二步”,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中国自身提出来的一套价值观体系,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如此一来,从“东方他者”这一问题出发的理论研究,就可以无缝地对接与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战略,为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这样的一种进路,与萨义德的激进立场和周宁的国家主义解决方式相比,其优点是显然的。因为,萨义德的激进离场重在“破”,而不是在“立”,在这一点上,萨义德和立场与福柯相似,他们内心里都隐藏了一种对“建构”的担心。任何一种形式的建构,都有可能变成遭到意识形态污染的产物,从而扭曲作者的意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萨义德和福柯归入到“否定主义者”(negativists)的行列当中去。周宁运用了萨义德的分析框架,那么,他同样没有办法避开这种分析框架当中所蕴含的价值承诺,因此,在分析的末尾,这种“建构”的幽灵(即“如何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建构”的问题)就出现了。
如果说批判和解构就是在原来封闭的西方中心论这个圆圈的圆周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建构的意义在于,重新在圆周周围的空白之地上划定出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可以由虚线或者实线构成,这种“虚”和“实”,代表着作者建构这种可能、替代范围的力度。如果作者提出的是一种强势版本的替代方案,那么就是“实”;如果作者采取一种弱化的立场,认为自己提供的不过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或者建议,而且本身并不具有十分强烈的范导性价值和功能,那么,这就是“虚”。但是不论是“实”或者“虚”,这都是在打开缺口之后作者需要进行努力的一个方向。周宁在运用萨义德的批判立场来对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目的论的“现代性叙事”进行解构的同时,他同样继承了这一困扰激进立场的“批判—建构”难题。周宁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否则他不会提出一个带有强烈“国家主义”意味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仅仅只是问题的一面。实际上,在提出这种“与权力联姻”的建设构想之后,周宁还提出了另外的一种设想方案。这就过渡到我们在接下来要分析的跨文化形象学的另一张面孔:“超脱于权力的立场”。
二、跨文化形象学的第二张面孔——“超脱于权力”
周宁之所以在“建构”这一问题上着墨不多,也是因为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一建构过程当中出现的“权力关系难题”,这造成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一方面,他意识到了建构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与权力联姻”却可能会打开一个潘多拉的盒子,造成许多“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
首先,他意识到,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在转化语境,与权力联姻了之后,就有可能就会被权力和民族主义绑架的局面。“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揭露西方现代性文化观念中的霸权结构的同时,可能遮蔽西方现代性的开放与自我批判的机制,使后发现代化国家与民族产生扭曲的现代性心理。同一种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意义呈现往往不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它产生的西方文化语境中,意味着西方文化自身的开放与包容性以及自我反思与批判的活力。而在那些后殖民或后半殖民的社会文化中,却可能为褊狭的文化保守主义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所利用,成为排斥与敌视西方甚至现代文明的武器”[8]。在这里,周宁明确地意识到后殖民主义文献在跨越文化语境之后可能会展现出来的不同面貌,这是一个典型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究其根本,乃是因为其背后隐藏的“与权力的关系”的问题。一方面,在西方的语境中,后殖民主义作为文化批判与西方主流社会中的政治权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是带着一种“解放的认知旨趣”(emancipatory cognitive interest)[9]去审视西方社会对非西方社会的霸权结构和文化支配。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讲,这种批判精神才表现出一种谦逊和开放的态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周宁尽管挑战了“启蒙诸理由”的“普世性”,但是他并未走向极端,认为我们就可以由此“打倒”启蒙时代遗留给我们的这一套价值观。他的批判态度是克制的,认为我们在意识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霸权性的同时,应当看到其自身当中“开放性、反思性、包容性”的一面。由此,我们在审视西方构建“东方主义”之时,就应当看到它代表了“西方现代世界性扩张的两个精神侧面。这两个精神侧面:一表现为是霸道的、褊狭的、傲慢的沙文主义与种族主义态度;一表现为谦逊的、开放的、反思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态度”[10]。并且,这种值得肯定的侧面是和西方的文化自信息息相关的。“只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才能产生并容纳这种否定性的自我批判。只有容纳这种自我批判,才能保存精神的自由与文化的健康。只有通过这种文化忏悔机制,才能达成并维持一种道德平衡,使扩张造成的文化紧 张不至于崩溃。西方现代文明最有活力的结构,可能就是这种包容 对立面的结构,从政治民主的自我监督到文化批判的自我否定”[11]。
但是,在另一方面,当这种文化批判被输出到非西方国家之后,则往往和民族主义、权力、民族解放运动勾连在一起[12],容易走向极端,在否定西方现代性当中霸权结构的同时,把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成就也一并否定,从而“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因此,周宁认为,“如果东方主义是西方甚至世界现代性规划的组成部分,超越现代性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批判的途径却没有提供建设的前景。……于是新的危险出现了,一是反现代化的带有愚昧主义的本土主义倾向,它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前现代的东方社会就是牧歌田园。二是鼓励一种文化自大与封闭的民族主义激情”[13]。因此,这种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本身所包含的那种反思,在民族主义激情的利用下,就变成了毫无节制地全盘否定。这种盲目的民族主义激情又非常容易地受到政治权力的利用,在否定西方的同时为自己增加合法性,同时为文化自大和自我封闭提供文化上的证成。因此,在非西方国家,这种批判精神容易变成一种民族主义激情,并受到政治权力的腐蚀。
因此,与前面“与权力进行联姻”的方案不同,跨文化形象学其实还隐藏了另外一张面孔,那就是对权力的警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在心理上的超脱与距离感。这样一种“超脱于权力”的面相,是糅合了如下的两种态度:一是对西方霸权进行克制的批判,二是对非西方语境中被狭隘民族主义滥用的警惕。
正因为如此,周宁才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案的设想,那就是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全球主义”或者“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以此来取代“东方主义”或者“西方主义”,既“要破除东西方地缘政治与文化的偏见束缚,也要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偏见”[14]。在这个设想中,周宁要达致的最终目标是“超越性”的(transcendental)。在他看来,“最终超越东方主义的途径,不是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二元对立的格局内,从一方转向另一方,……而是采取一种强调同一与连续性的态度,强调世界历史发展中不同文明互动的关系,强调不同种族、文明之间的所谓‘跨文化空间’或‘跨文化公共空间’的发展动力,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分界不仅是相互对立与排斥的过程,同时也是超越界限、互通有无、互渗融会的过程,强调‘文化间性’的思维模式”[15]。
结语
由此可见,周宁在批判与建构之中,其实表达了一种矛盾的态度。他希望跨文化形象学不止步于仅仅进行解构性的批判,在此基础上,他还希望能够进行一种积极的建构,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在这种积极的建构之中,则必定无法回避文化批判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权力是可以助推我们用特定的文化政策和战略来进行实现某种目的[16]。但是,权力作为一把双刃剑的特性,致使我们可以模糊地预见,知识与权力的联姻很有可能会带来我们无法预见的“未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17]。更有甚者,权力的污染可能会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恐怖的小孩”(monstrous child)[18]。正是这两个相异和相互冲突的方面,构成了周宁在批判和建构之间这种举棋不定的暧昧态度。
但是,我们对周宁的这一观察,必须要被放置到一个“同情式理解”的语境当中,否则就落入“为批评而批评”的窠臼。在我看来,周宁之所以要在最后提出这样的一个建构,本身是带有一种比激进左派更为深刻的关怀。周宁是否意识到自己立论过程当中的二律背反,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不谈;但是,周宁之所以要进行“建构”,显然从动机上讲,是因为他不满意于仅仅做批判,这样的一种建构,本身不是产生于“在‘破’之后就一定要去‘立’”这样的一种冲动,而是体现着对批判和怀疑态度的反思,这样的反思,是学者严谨地审视自己内心的一种结果。正是这样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才让周宁去试图建构一个积极的行动方案,来挑战或者改革他立论中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景象[19]。在超越了“为建构而建构”以及“为批评而批评”之后,周宁的这种批评和建构本身都带有一种朝向自我(inclined towards the self)的内省倾向。

